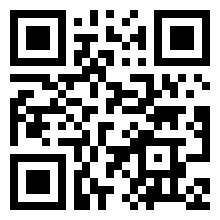刘顺峰:八年突破“一厘米”

这个光纤连接器顶端1厘米多长的白色接头耗掉了他的8年时光、1亿多元。
人物简介:
刘顺峰:瑞安市人,高级工程师,现任苏州中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,2008年曾被江苏省委组织部列为“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优秀人才”,被誉为“民营企业科研创新精神的代表”。
他负债一亿多元,但债权人们却主动要求,把债务转化为公司10%左右的股权;
他们的产品还处于小规模生产状态,就有大型通信企业过来希望签下30亿元的订单;
他们被寄望以在温州带动一个数百亿的光通信制造基地,在其产业化还未真正实现时,愿意为其配套的企业就已络绎不绝;
因为在陶瓷插芯的制造工艺上打破日本垄断,拥有自己真正的核心技术,刘顺峰的“中光科技”一跃成为市场与投资者们眼中的“香饽饽”。
这位土生土长的温州老板,凭什么在无数科研机构、跨国公司都一筹莫展的科研难题上取得突破?
“这东西比黄金还贵”
1999年,一只光纤连接器大约可以卖到40多元。它的组件中,最贵的就是前端那一小段白色的接头,每只值3.2美元。
当时,黄金的价格每克仅约80元,而陶瓷插芯那只有0.1克左右的组件,却值25元。刘顺峰算了一笔账,立马决定改变思路:不做组装工厂,自己研发,一定要拿下那一厘米比黄金还贵的小玩意。
那一年,刘顺峰身家大约为5000多万元,此前他办过工厂,做过贸易,同时还野心勃勃地准备进入地产行业。
他并不知道,他发现这个商机的前后,日本的京瓷、东瓷等企业,已经放弃了长达10年的尝试,他们尝试的方向,正是刘顺峰今后所要选择的。
昂贵的“土法研发”
2002年,刘顺峰的实验室成立——它是由父母在农村的猪圈改造而成的。当时,他还不知道如何描述插芯里那个120微米的小孔,他告诉研发团队——“这个孔大概是一根头发丝那么大”。
他知道那个东西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锆,但他还是尝试着买了一些二氧化锆——那是打火机中打火石的主要成分。他甚至觉得这两者应该没什么区别。
二氧化锆每吨4万元,浪费不了多少钱。但氧化锆就贵了,日本进口的每吨120万元,国产货每吨48万元,有时候,一天就融掉200多公斤的粉末,十多万元就这样没了。
没有配套的研发,成本往往是几何级增加。比如做模具时切割一块钨钢,钨钢只要600多元,但需要人员专门赴外地去采购,然后送到乐清去切割,拿回来一试不合格又要再送再切,来来回回,成本能从600元飙升到近万元……
原来是个“863项目”
2005年,在一次向专家请教的过程中,刘顺峰才知道,自己居然“不幸”被套入一个“国家863项目”。
“国内陶瓷领域的最权威机构硅酸盐研究所,从2000年就开始投入研发,至今尚无成果。你们怎么敢投入去挑战这个东西?”
刘顺峰拿出“土法制造”的一个样品,做好了放弃项目的准备。但对方在仔细看过之后,却颇为慎重地对他说,“你们离成功已经很近了。”
“其实还远着呢,后来我才明白过来,这只是一句客套话。但如果没有这句话,当时或许我就放弃了。”他这样回忆道。
那一年,在经济上,刘顺峰实际上已经破产了。
“你就是那个破产的民营企业家”
2007年,刘顺峰再次陷入技术瓶颈。
这时他已经在国内这个领域的大部分专家中都混到“脸熟”了,一个上海的朋友为了引见,给了他一次拜访“中国光纤之父”、 中科院院士黄宏嘉的机会。
“我知道你,你就是那个搞到破产的民营企业家。”黄老先生说。
老院士拿出纸张,从原材料开始,为他分析这个项目可能突破的几个方向……
“一个晚上的谈话,解决了我们大约30%的问题。”刘顺峰感慨总结说,以他的项目为例,靠着民间的土办法,解决到40%其实已经是极限了,在那以后,都是高端技术人员才能解决的问题。
2009年,双向定位干粉干压成型法在张家港取得成功。瑞安农民企业家刘顺峰被列入江苏省科技厅高级专家库。
今天,黄金的价格涨至每克320元以上,而陶瓷插芯则跌至每只2.5元左右,价比黄金已成历史。所幸其用量比当年不知涨了多少,庞大的市场空间依然能为其带来诸多效益。
做人方式决定我的成功
记者:在创业者中,执著于自己的选择,并且如你一样不计代价投入的人并不少,以一个成功者的经验,你对他们有什么忠告?
刘顺峰:我觉得坚持自己的选择很重要,但你首先要了解自己,你有没有能力坚持,你的性格、人脉关系能不能为自己找到帮助。比如我一度负债达到1亿多元,曾经6个月发不出员工工资,8年来公司没有任何产出,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做人方式,让借钱的朋友相信我,让员工不离开。如果做不到这些,你坚持再多也没用。其次,做一个高科技的东西,一个人本事再大、学历再高也没用,最终还是要靠团队,靠各种高端人才的头脑,要利用好这些,其实最终还是回到如何做人的问题上。
记者:以你当年五六千万元的身家,如果不做这个项目,今天可能创造更多财富。你觉得如今你得到的足够了吗?
刘顺峰:如果我一直做房产,今天可能更成功。但选择了这个项目,有了那些经历,对我个人的人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完善过程。从这个角度讲,那是很值得的,但是回想这个过程中的痛苦,我常常还是觉得代价太大了——十年来,我12点之前睡觉的次数不会超过30次。